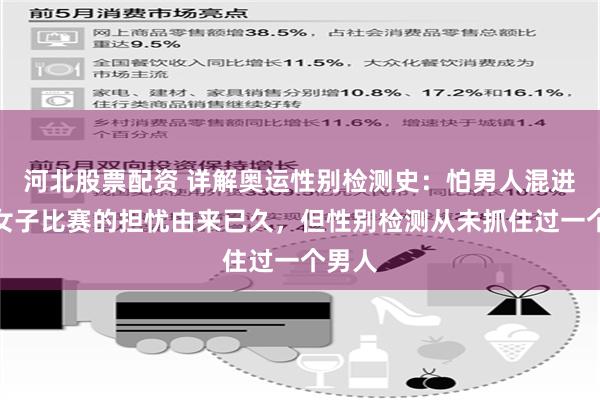
夏尔马提到,最近美元的疲软提振了比特币,因为人们开始购买“数字黄金”来对冲美元疲软的影响。他指出,不那么精通技术的人仍对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持怀疑态度,但年轻人更喜欢加密货币。
巴黎奥运会上变性人/男人混进女子拳击赛的争议中,不少人提出奥运会需要有性别检测,防止男人装作女人。还有人指出只要有Y染色体就不是女人,不该被允许参加女子比赛。
可有很长一段时间奥运会对所有女运动员做性别检测,染色体检测还是使用最久的方法,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防止男人混进女子比赛。因此,很多人听说奥运会性别只看护照后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怎么也要加入染色体检测才行,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奉为圭皋的东西,纯属老黄历。而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些性别检测从未抓住一个男人,倒是伤害过不少女人,还很早就被科学界指出根本不靠谱!
1.女人踏上赛场的第一天,是不是女人的争议就开始了
怀疑有些女运动员不是女人在现代奥运会之初就有。奥运直到1928年才有女子田径,此前女性都只能参加帆船、网球、高尔夫等时人认为适合女人的活动。那个时代很多人真切相信如果女人不断锻炼,身体越来越强,有可能会变成男人。近百年后,大多数人应该能同意前辈们的担忧毫无必要:男女之间的玻璃天花板远没那么容易打破。
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日本女运动员人见绢枝在800米比赛中以2分17秒的成绩获得银牌(下图左为奥运会上的人见绢枝)。

人见绢枝身高1米69,完全不符合当时西方对东亚女人娇小纤弱的刻板印象。奥运会组织者专门搞了委员会,对人见绢枝检查、审问了两个多小时,她可能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被检验女儿身的选手。按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的报道,结论是人见绢枝是“它”不是“她”。
阿尔及利亚女拳手Khelif与中国台湾女拳手林郁婷不是女人的谣言能传播如此迅速,和近百年前人见绢枝被检查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她们看着不像人们印象里女人的样子。
但奥运会不是选美,更高更快更强,意味着不少女运动员都更魁梧壮实。自然让看客有了“是女人吗”,或者“莫不是男人”的质疑。可很多被用来证实性别检测必要性的男人混迹女子比赛的故事都被演绎得偏离事实十万八千里。
不少当代媒体甚至学术研究会叙述30年代纳粹德国让一个男人将自己的生殖器贴身束好,参加女子1936年柏林奥运会。该故事的主人公是Heinrich Ratjen,但纳粹将男人混入女子奥运项目是西方媒体后来的脑补。
真实情况是Ratjen大概属于生殖器官没有显示出明确的男女特征,其父亲回忆,产婆一开始说是个男孩,很快又改口说是个女孩。Ratjen从小就被当做女孩养,她也以为自己是女孩子,一直参与女子田径,1936年,17岁的Ratjen(下图左)参加了在自己祖国举行的奥运会女子跳高比赛。

不过当时没人怀疑Ratjen的性别,甚至她的队友们也没有。Ratjen是1938年偶然在一趟列车上被一位警察质疑是男人,要求做检查,才被认定为男人。当年的检查没有详细记录,从一些保留的文字看,检查医生认定Ratjen是男人,可也有一位医生写了这个人的生殖器官绝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发生关系。这让Ratjen到底属于什么情况仍不清楚,可此后Ratjen的身份证明重发,登记为男人。
但30-40年代奥运会里担心有男扮女装的想法并不少。当时的处理方式是组织者凭感觉,看谁不像立刻带走审查。同样在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女子100米比赛中美国运动员Helen Stephens(图左)击败卫冕冠军波兰选手Stanisława Walasiewicz(图右)获得金牌。当时很多人尤其是波兰媒体,质疑Stephens可能是男人,否则怎么能击败夺冠热门Walasiewicz。

柏林奥组委对Stephens做了“详尽检查”后,宣布她真的是女人。这个性别疑云在40多年后出现了颇为讽刺的逆转,1980年,已经移民美国,将名字改为Stella Walsh的Walasiewicz在一次抢劫案中不幸遇害。由于是暴力死亡,她的遗体做了法医检查,发现原来她是间性人:没有包括子宫卵巢在内的女性生殖器官,有发育不全的阴茎,很小的睾丸与前列腺。她的染色体存在嵌合,大部分细胞是XY,一些是XO。
一些关于奥运会性别检测的叙述中,Walsh被描述成了检测必要的证据:1932年奥运女子100米冠军死后被发现有睾丸。可实际上Walsh生前从未被怀疑过不是女人。
Walsh的时代——女子运动刚刚进入奥运的时代,人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刻板印象来怀疑谁可能不像女人,让一些自己眼中不像女人的女运动员去接受检查。可这些检查没找到一个男人。
2.从裸体游街到染色体检查
1936年奥运会时,强烈要求做全面性别检测的美国奥委会主席Avery Brundage(后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提出1940年奥运会必须查女运动员性别。若非二战爆发,按30-40年代赛场性别疑问的发展趋势,奥运会的普遍性别检测应该能更早成型。不过随着冷战开始,历史很快就衔接上了。1946年,国际田联(现世界田联前身)要求女性运动员携带证实自己是女人的医学证明。1948年伦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参照了这一做法,所谓女人卡(Femine card)出现了。
可女人卡没有打消看客的担忧。尤其是东欧女子运动的崛起。西方媒体对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女性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出色的成绩满腹狐疑:是不是派了男人来诈骗奖牌?当然,这种怀疑不只针对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罗马奥运会,两名英国女运动员也被怀疑是男人。
显然,让每个国家发女人卡靠不住。1966年,欧洲田径锦标赛第一次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做了系统确认:所有女运动员必须由三名女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检查生殖器、性征。
此类检查后被批为裸体游街(nude parade)。有些赛事中的性别检查甚至都不是看看就好,1966年英联邦运动会,有名运动员将性别检查形容为被猥亵。1967年泛美运动会则明确要求是物理检查。
检查也充满了随意性,67年泛美运动会的一位运动员回忆当时有位瘦小的田径运动员被医生告知自己上面不够大,不能参赛。
这些体检从未找到过一个男人,甚至名义上都没有一名运动员由于没通过体检被禁止参赛。像“上面不够大”的女运动员,实际是被医生们私下劝退,并非不合格。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女性运动员被如此劝退。
裸体游街显然不受欢迎。正当国际奥委会为如何鉴别女人发愁时,科学来救场了。1948年,加拿大科学家Murray Barr发现了巴尔体: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可女性的一条X染色体会失活,避免表达双倍基因,而失活的X染色体有着特殊的巴尔体形态。
秉承送佛送到西的精神,1955年Murray Barr与人合作,开发了口腔黏膜涂片,刮取一些口腔上皮细胞,就能检查巴尔体,即对性染色体做初步检测。
和女人卡与裸体游街一样,巴尔体这类性染色体检测也是国际田联最先使用,后被奥委会等赛事组织者称为遗传检测。1967年,在基辅举行的欧洲杯国际田径比赛,遗传检测初出茅庐便有“斩获”。
波兰运动员Ewa Kłobukowska被国际田联的遗传检测查出“不是女人”。Kłobukowska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银牌,100米接力金牌得主,欧洲顶级短跑运动员。前述提到的1966年欧洲田径锦标赛里,她也拿到了100米金牌。该赛事对所有女运动员都做了性别检查,Kłobukowska显然通过了这种检查,被认定为女性。
但令人诧异的是1967年她在遗传检测里却没合格。两种检测完全相反的结果没有浇灭国际田联用新技术抓住假女人的兴奋,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兴奋过头了。国际田联满世界宣称Kłobukowska多了一条染色体(one chromosome too more),不仅取消她的参赛资格,还将她过去的所有成绩记录全部剥夺。Kłobukowska也遭受了公开羞辱。
国际田联的清理工作是如此细致,以致我们现在都很难找到讲述她过去成绩的故事。
60年代人们对遗传检测的高度信任,以及国际田联的成功实践,让国际奥委会也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正式启动基于巴尔体的性别检测。国际体育赛事的女人鉴定全面进入遗传检测时代。不过奥委会在Kłobukowska事件中学到了一个教训:不公开结果,防止类似的公开羞辱重演。
3.被遗传学家质疑的遗传检测
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Kłobukowska事件,我们能看到这个鉴别出所谓假女人的遗传检测问题重重,其实都不用半个多世纪的冷静期,如果当年国际田联与国际奥委会多用上半身思考,就会发现自己不是有重大发现,而是出了重大事故。
首先,国际田联的检测结果是多了一条染色体,应该是说Kłobukowska在两条X染色体外还有一条Y染色体。由于有两条X染色体,Kłobukowska若是在一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能通过巴尔体检测,会被认为是女性。这意味着不同遗传检测并不一致。目前认为Kłobukowska很可能是具有嵌合性,即部分细胞有Y染色体,这种情况更不能凭部分细胞里有Y染色体就认定不是女性。
其次,Kłobukowska是通过体检认定的女人。也就是说她的生殖器、性征等都符合女性特征。这本应让赛事组织者对遗传检测的适用性有所警觉。
最后,也是最讽刺的一点,据报道,被公开羞辱的Kłobukowska于次年,1968年怀孕诞下一子。
如果你问我,一种性别检测鉴别出来的第一个不是女人的人,不久后怀孕生子,我的反应会是这种性别检测也忒不靠谱了。但国际大赛的组织者们竟然没有看到这都不能更亮的红灯,接下来的30多年里,遗传检测几乎是所有奥运会女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参赛体验,只有一位女运动员免于检查,大家可以猜猜是谁。
当奥委会、国际田联自认为找到了确保女子比赛都是真女人的锦囊妙计时,科学家们震惊了:这种所谓的性别遗传检测完全不科学!
许多遗传学家在奥运会采用遗传检测后都质疑这种检测的可靠性,提出理论上这既不能抓住所有假冒女人的男人(有少数男性具有XX染色体),抓出来的也未必就不是女人。
抗议的遗传学家们很多都是奠定了人类性染色体研究的学界大咖。其中最早提出质疑的一位科学家是芬兰遗传学家Albert de la Chapelle。de la Chapelle最著名的学术贡献是阐明了Lynch综合征(一种让癌症发病率大增的遗传病)的遗传基础。此外,他在只有单条X染色体的特纳综合征,具有XX染色体的男性的性别决定机制等领域,都有奠基性研究。XX染色体男性也被称为de la Chapelle综合征,他在该方向的研究促成其他科学家克隆鉴别出雄性决定基因SRY。
早在1982年,de la Chapelle就给奥委会写信,指出所谓性别遗传检测不可靠,可能对一些女运动员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在学术界估计没人会反驳de la Chapelle在性染色体上的权威,但在奥委会看来,你们这些科学家懂什么,无非是发现或发明了我现在使用的检测而已。将近一年后,一位奥委会成员回信告知de la Chapelle,遗传检测确实不是最安全的检查,但它经济实用。你和我讲科学,我和你讲经济。
de la Chapelle不愿放弃,坚持给各个医学委员会乃至奥委会主席写信,却无人理睬。屡屡劝谏无果的de la Chapelle在给英国遗传学家Martin Bobrow爵士的一封信里表示“除非出现一个重大丑闻,我对改变这一切非常悲观”。
历史证明de la Chapelle没说错。
4.不愿隐退的女人
奥运会采用遗传检测后有一个神奇记录:从来没有一名女运动员因为没有通过检测而失去参赛资格,就像裸体游街时代没有一个女运动员不合格一样。
如果你对人类性染色体的复杂性稍有了解,就会意识到,在那个国际赛事里女性运动员越来越多的年代,按人群中不符合经典XX/XY性别的比例,奥运会没人不合格根本就不符合统计学!
实际上不光是奥运会,所有国际大赛里除了第一个撞上枪口的Kłobukowska,近30年就没人不合格过。
赛事组织者宣称是因为遗传检测的存在,吓得假女人们不敢以身犯险,所以大家都合格了。可当一些事不符合统计学规律时,真相往往是有人在篡改规则,遗传检测也是如此。
据一些人回忆,其实每届奥运会都有至少一两名女运动员没通过性别检测。遇到这种情况,赛事组织者会劝运动员假装有伤退赛。这些运动员大多也不希望自己像Kłobukowska那样被羞辱,只能听话退出。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会事先对自己的运动员做检测,避免在大赛上被检出假女人的尴尬。
但1985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遗传检测遇到了第一个不愿闭嘴的女人:24岁的西班牙运动员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
Martínez-Patiño(下图)是出色的跨栏选手,在当时西班牙不重视女子体育的情况下,她是该国第一位拿到体育奖学金的人,还凭此搬到了马德里一个体育中心的宿舍,她也是该运动员宿舍唯一一名女生。83年田径世锦赛,她的100米栏成绩是13.78秒,获得参加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但在84年,她唯一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为了挽救弟弟的生命,一年中她多次捐献骨髓。可惜她不仅没有救下弟弟,还因这些骨髓捐献没法正常训练,错失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来到日本的Martínez-Patiño期待着比赛的开始,走出过去一年的阴影。她在两年前的田径世锦赛上已经通过了性别检测,有女人卡(为了节约成本,各项大赛一般都会承认过去的遗传检测结果,避免重复检测)。但机缘巧合,她和队友们将女人卡拉在了西班牙。于是,她们被赛事组织者要求做性别检测。由于过去查过,Martínez-Patiño没太当回事。可在第一次被刮了口腔做口腔涂片检测后的第二天,队医告知Martínez-Patiño她还要再做检测,这次包括血检。再往后,队医告诉她,你不能参赛,装有伤。
其实1985年的大学生运动会上,至少还有一位女运动员没通过遗传检测:美国游泳运动员Kirsten Wengler。她却被允许参赛。一种说法是当时赛事组织者没有额外的人力对Wengler做进一步的妇科检查,因此没将她除名,但Wengler本人认为是因为自己并非“肌肉女”,外表符合西方传统白人女孩形象。另外,相较田径,游泳也被认为是适合女孩的运动。(回到美国后,Wengler在家人安排下又做了检测,显示之前的结果是假阳性)
Martínez-Patiño没那么幸运,不仅被迫成了观众,回到西班牙后还被皇家田径协会劝说退役。1986年初,她报名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的60米栏,被田径协会警告最好悄悄退赛,如果参赛,就公开她的情况。但Martínez-Patiño决定不再服从组织安排,在赛场上做回自己——她拿了金牌。
很快,Martínez-Patiño就明白了不听话的代价:一夜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她为何在日本退赛。几乎所有的西班牙报纸甚至很多国外报刊都刊发了她的照片,配上文字:女子跨栏冠军有男性染色体。她的医疗记录在全球传播。Martínez-Patiño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感觉就像是被人强暴,而且是在所有人围观的情况下被人强暴。
将近40年后,Khelif与林郁婷的经历与之有着令人恐惧的相似。当然,一个显著的区别是试图羞辱Martínez-Patiño的人至少拿出了真实的检测报告,不是号称有检测结果。
Martínez-Patiño的灾难才刚刚开始:田径协会取消了她的奖学金,将她赶出运动员宿舍,清除她的所有记录。他们要像抹去Kłobukowska一样抹去Martínez-Patiño曾经在田径场上存在过的痕迹。她有两个选择:继续与田径协会以及性别检测政策为敌,面对更多羞辱,或者和过去无数性别检测失败的女运动员一样,接受命运,悄悄离开竞技体育。
有时,只有当你决定反抗时,才会发现貌似强大的对手其实非常脆弱。马德里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鼓励Martínez-Patiño不要放弃,并给她看了de la Chapelle在JAMA上发表的论述染色体性别检测不可靠的划时代论文,这篇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隔年又被分别翻译成意大利语与日语刊发。
Martínez-Patiño将西班牙皇家田径协会告上法庭,申诉国际田联的禁赛决定。1986年,西班牙当地法院判皇家田径协会向Martínez-Patiño赔偿2000万比索,作为非法大规模散布隐私信息导致伤害的惩罚。
她也联系上了de la Chapelle,后者从科学上为她解释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她有XY染色体,但由于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并没有男性的身体优势。
de la Chapelle为Martínez-Patiño提供科学上的意见与支持,帮她联系上同样有医学研究背景的国际田联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Arne Ljungqvist(后来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创始董事)。在de la Chapelle亲自辩护与Ljungqvist的帮助下,国际田联在1988年恢复了Martínez-Patiño的参赛资格。
Martínez-Patiño的公开抗争,也激励了无数遗传学家、内分泌学家、妇科专家,TA们纷纷指出使用染色体作为单一的性别评判标准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医学伦理。
在潮水般的抗议声中,1992年,最早采用染色体检测的国际田联终止了“遗传检测”。90年代,奥运会放弃巴尔体检测,转而使用PCR技术检测Y染色体上的特定基因,1999年,在学界反对以及大量数据显示遗传检测徒劳无效后,奥委会宣布终止遗传检测。
经历了两年的停训,不断申诉,Martínez-Patiño艰难尝试重回赛场,可在1992年,她因0.01秒的差距没能获得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她的个人最佳成绩停留在了83年世锦赛的13.78秒。若非85年偶然忘了女人卡,Martínez-Patiño或许会是不止一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但这次意外后的奋起反抗,让她做到了很多奥运冠军都无法做到的事:改变世界。
5.注定失败的遗传检测
站在科学角度,奥运会乃至整个国际体育界30多年的染色体性别遗传检测的失败是注定的。令人惊讶的反倒是从一开始就被学术界,包括那些性染色体、性别决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们质疑科学性的检测方法居然能持续如此久。
性别并非很多人想象那样二元分明。人的性别认同受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影响。甚至仅看生理性别的决定机制,也不是XX/XY染色体就能明确划分。
XY性染色体发现于1905年,对那些认为Y染色体是鉴别男性金标准的人,我的疑问是:1905年以前,你如何知道谁是男人,谁是女人?性别区分远早于XY染色体,人类也有除了XY染色体以外的性别鉴定方法,例如外生殖器、第二性征。绝大多数人的性别鉴定也就是出生时在医院看外生殖器确定(B超查性别也一样)。
当然,这些“外观”在人群里有巨大差异,会有模糊状态,这应该是Heinrich Ratjen被当作女孩,后来又被认定是男人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国际体育界66-68年的裸体游街更像是闹剧。可看似二元分明的性染色体也只是性别决定机制的一部分——绝大多数XX染色体的人会有着女性性器官发育,XY染色体会有男性性器官发育,但具体性别发育绝非有什么染色体就是什么性别那么简单。
性染色体背后是多个与性别决定相关的基因,它们又调控着很多与性器官产生、发育相关的蛋白、激素。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极度简化,勉强可以概括成人类Y染色体上有SRY基因,它可以视作人类雄性生殖系统发育的总开关,SRY基因的表达会开启一系列与雄性生殖器官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包括让个体产生较高的雄性激素睾酮。睾酮可以被一个叫5-AR的酶改造成二氢睾酮(DHT)。在睾丸从腹腔下降到男性外生殖器发育角度,DHT的作用会大于睾酮。
当一个人有Y染色体,准确说应该是胚胎,因为Y染色体主导的性别分化从妊娠7周时就会开始,从SRY基因表达到睾酮形成再到DHT,性腺、生殖器发育会成为我们定义的雄性/男性。
但如果有人有Y染色体,SRY基因却缺失或无法表达呢?或者雄性激素起作用的关键——雄性激素受体,功能缺失呢?或者5-AR功能缺失(5-ARD),没法将睾酮转变为DHT呢?
这些“意外”都会让Y染色体决定的性别发育有变。比如SRY基因缺失的人具有XY染色体,但生殖器官以及其它与性相关的表型会是女性,而性腺功能缺失,也被称作Swyer综合征。
而Martínez-Patiño虽然有XY染色体,却因为雄性激素受体上的突变,导致雄性激素没法起作用,这叫AIS,根据雄性激素失效的程度,分为彻底失效的CAIS,与部分失效的PAIS。CAIS除了内部生殖器官——没有卵巢子宫,有发育不全的睾丸外,性征也是女人的性征。
PAIS与5-ARD则根据个体情况,性器官会有很大变化,有的更像男的,有的像女的,还有一些会是中间状态。而现实中,出生的婴儿如果出现生殖器官不那么能明确性别,更有可能会被归为女孩。
这些特殊的性别发育表现如今被统称为性发育差异,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简称DSD,过去常见说法是间性,intersex。DSD在人群里的比例可达2%。取决于DSD的具体类型,奥运会曾经采用的染色体鉴别女性有“惨不忍睹”的表现:

Martínez-Patiño这样表型是女子的AIS运动员在巴尔体检测等染色体检测里被认为是假女人,而具有XXY染色体或XX染色体(少数情况下SRY基因可以重组到X染色体,就能出现具有XX染色体的男性)的男人,却能顺利过关。
这还只是一些常见的DSD,没有涉及嵌合体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体内可能出现不同细胞有不同的性染色体组成。像因遗传检测不合格被羞辱的Kłobukowska很可能有这种嵌合。
在你准备说嵌合体是阴阳人不正常之前,一个基本常识:最常见的性染色体嵌合现象是男性的Y染色体丢失。实际上只要男人活得够久,就很有希望遇到Y染色体丢失。70岁男性当中,40%以上血液白细胞存在Y染色体丢失。当然,年轻男性Y染色体丢失比例较低,也不太可能有70岁的大叔参加奥运会,可在奥运会男子网球冠军37岁,美国男篮领军人物39岁的时代,最好不要对Y染色体有太多假设。
Kłobukowska因为有部分细胞存在XY嵌合被认为多了条染色体不是女人。那我作为男性,如果部分血液细胞出现Y染色体丢失,是否也不再是男人了呢?或者如果有10%的血液细胞丢失了Y染色体,就是九成男?显然很荒唐。顺便说一句,IBA的俄罗斯主席说Khelif和林郁婷有Y染色体,不是女人。我非常期望他自己能去测一下有多少细胞有Y染色体,让世界知道他还剩下百分之几的男人。
de la Chapelle等遗传学家正是因为深知染色体检查确定性别的问题,才会坚决反对。若非Khelf与林郁婷面临着真切的网络暴力甚至是人身威胁,20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宣称染色体检测的准确性,都可以说是有喜剧色彩。
6.无用也无必要的性别检测
不仅是奥运会过去使用染色体遗传检测查性别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同样可疑的是其必要性。性别检测的倡议者们总会说如果让男人或非女人混进了女子比赛,对参赛的女人们不公平。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稍加剖析就会发现虚伪。
从奥运会最初的性别检测起,就是针对不符合传统女性形象的女运动员,是社会将女性纳入刻板印象规范的延伸。日本女人怎么能有1米69,所以人见绢支需要被审查。加入性染色体后的“科学”也只是一种表演——同样没有通过遗传检测,白人小姑娘Wengler照样可以参赛。为什么?因为这些性别检测从来不是让女运动员得到公平待遇,只是为了有机会赶走那些看不顺眼的“女人”,以公平为借口维持一个不公平的世界。
记得前文提到的从1968年到1999年,30年间奥运会只有一位女运动员免于性别检测吗?你猜到是谁了吗?答案是英国的安妮公主。安妮公主与许多英国皇室成员一样,热爱马术,而且她还精于马术,参加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马术比赛。

为什么安妮公主不做性别检测?呃,奥委会与赛事承办方能去质疑一位公主的性别吗?但对马术比赛的任何一位女选手做性别检测的意义在哪里呢?奥运会马术比赛是极少数不分男女两性直接竞争的项目。真的需要担心有男人假扮成女人进入马术比赛吗?
同样值得思考,奥运会以及国际体育赛事的性别检测只针对女性。既然担心男人混进女子比赛到需要对女性选手做系统验身时,为什么不担心女人混进男子比赛呢?男女生理差异意味着女选手进入男子比赛肯定不占优势?那些更考验精细、平衡或柔韧性的项目里,女性没有性别优势?
认为没有性别检测,男人能混进女子比赛,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实情。很多比赛项目的着装都很显真身,飞行药检等当代反兴奋剂的严格管理,更意味着高水平运动员常常要当着药检员的面提供尿样。一个生理结构是男性的运动员能混过去吗?
想象男人混进女子奥运赛事对女性运动员造成不公,也小瞧了顶级女运动员的水平。很多项目,最优秀的男运动员确实比女运动员有显著优势,女子百米至今未破10秒大关,而10秒已是参加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入场标准。这给人一种男子赛事水平远高于女子的感觉。可要注意全世界也没多少男人可以达到顶级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巴黎奥运女子百米的入场标准是11秒7,有多少男的可以跑进这个水平?能跑进这个水平的也会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可能去乔装女人参赛吗?就是想装,能成吗——跑到这水平,也会是受到关注的运动员,不是随便哪个路人甲。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奥运会性别检测抓不到男人:能和奥运女选手比肩的男人不想装或装不了;就算有想装的男人,能力不行。
如今参加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选手,不论男女,都是咱人类这个物种里运动水平的佼佼者,也会是各项目里早就排了号的,就算那些你觉得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一鸣惊人的,之前大概率也在青年赛事或洲际赛事里大放异彩过。像叶诗文16岁在12年奥运会一战成名,可人家两年前14岁在亚运会就游出过全球年度最佳。
奥运会性别检查看看护照就行,是因为那些个参赛者对赛事组织者来说都是熟面孔。这也是为什么IBA指责Khelif与林郁婷不是女人很荒唐,人家参加顶级拳赛多少年了?当着药检官小便多少回了?睾酮在兴奋剂检测里测了多少次了?突然跑出来说别人不是女人,而且连个像样的证据都没有——Y染色体这种早就被学界指出不对的检测都没拿出检查报告,很多人居然深信不疑,长点脑子,好不好?
国际奥委会坚持到1999年才放弃遗传检测,只是在90年代将巴尔体检测改为PCR测SRY基因。也要感谢奥委会的顽抗,我们也能看到遗传检测的真实效力数据。

1972年起5届夏季奥运会,女运动员性别检测异常的比例一直稳定在400-450人中有1人。亚特兰大奥运会还有8例异常的具体情况鉴别。

8位运动员7位属于雄性激素不敏感,一位是5-AR缺失,有6人移除了性腺(gonadectomy,很多AIS患者确诊后会建议摘除性腺,即发育不良的睾丸,因为她们有更高的睾丸癌风险)。
这些被遗传检测查出来的都不是伪装的男人,她们的外生殖器、表型都是女性。实际在没有染色体检测等现代医学技术出现前,她们一直会是社会眼中的女人,不会遇到任何疑问。这也证明了de la Chapelle等遗传学家的看法:奥运会的遗传检测,并没有抓假女人的效果,只会对一些女性运动员造成伤害。
还要强调,像亚特兰大奥运会检查出来的8位属于DSD的女性,DSD不会让她们相对普通女运动员有明确的竞技优势,不会导致赛事不公。这也是为什么她们都被允许参赛。
一些人说DSD有更高睾酮,一,不是所有DSD都如此,二,查出的多位有AIS,她们的睾酮受体功能受损,不会因更高的睾酮有优势,那些移除了性腺的,更是连睾酮水平都不会更高,三,人体内天然睾酮本身不绝对对应运动能力,这与人为加入睾酮作兴奋剂不同。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需要另外解释。但总之,不能因为是DSD就认为在体育竞技上对普通女性存在不公平竞争。
奥运会女运动员中AIS比例似乎高于人群中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AIS选手身高普遍也高——Y染色体遗传物质会对身高有影响,如今有研究指向这会让AIS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运动员,毕竟很多小孩被选去参加体育往往是看重身高优势。可这不能说是对女性不公:篮球、游泳等很多体育项目都是高个子有优势,如果AIS身高更高就认为是不公平竞赛,姚明、菲尔普斯又该怎么算呢?
对于现在那些奥运会女子项目可能混入非女人的担忧,记住:从女人刚踏上奥运赛场的那一刻,这种打着保护女人,维护公平旗号的忧虑就有了。而真相一直是:或许有的女人真能跑那么快,真能跳那么高,真有那么强。
参考资料:
https://www.utpjournals.press/doi/pdf/10.3138/cbmh.28.2.339河北股票配资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股票在线配资网_手机配资股票_股票配资网站观点






